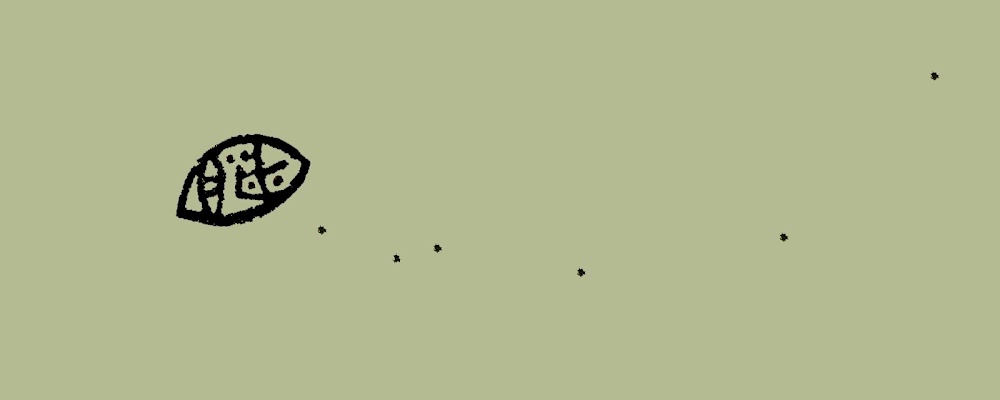「看不懂」可能有兩種意思。
一種是:「這文章到底在講什麼?」另一種是:「寫這個做什麼?」
毛毛蟲月刊最近的訂閱人數稍有進展,但還是不如預期。前陣子在國際研討會中推廣的時候,聽聞有人表示「看不懂」。楊茂秀老師與我自認裡頭沒有硬得難咬的學術性文章,那麼,「看不懂」指的究竟是什麼?
我想了想,想出開頭寫的那兩種意思。
如果是第一種:「這文章到底在講什麼?」那麼可能令人高興。某些文章,如果它是要誘使你思考,那麼就不會講得明明白白,就像莊子的寓言(我最近再次讀了莊子「無用之用」的寓言,還真是精彩!)這不是說毛毛蟲的文章都像莊子的寓言一樣精彩,而是,毛毛蟲的文章希望做的是:讓讀者有思考的空間(這點我們仍在繼續努力)。
第二種:「寫這個做什麼?」我就感到比較無力一些些,但我還是願意正視這件事。畢竟每件事情都有人覺得重要,有人覺得不重要;當我們認為重要的事,別人感受不到它的重要性時,或許我們可以努力的是——那麼要用什麼樣的方式,可以讓原本不覺得重要的人,試著接觸與瞭解。
最近開始規劃毛毛蟲改版,為的是要讓毛毛蟲讓更多的人看見。或者該這麼說:不是為了毛毛蟲,而是為了大家;這樣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,但真的是這樣——毛毛毛蟲有一些好東西希望能讓大家認識,那個好東西就是「思考」——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思考,是從小孩就該開始做的思考。但是,為什麼毛毛蟲要做這件事呢?
我已經說得太多了,快要過於明白了。現在該讓問題回到問題。
2010年8月31日 星期二
2010年8月30日 星期一
2010年8月28日 星期六
為什麼寫作?(一封回給友人的信)
L:
在上封信我本來想這麼回信:我並不覺得自己對文章的要求太高。但讀了你這封信,我想某種程面上,或許是;但也或許不是。
我回想自己小學六年級寫的東西,大概也沒有什麼所謂「進去的東西」。我真的意識到「寫」這件事的意義,以及它與我的關係的時候,已經是大人了。我很少後悔,但我真的這麼想過:要是我更早一點認識寫作,我想我會更早開始認識自己;一些覺得空空的日子可能也會少一點。
回到那位同學的作品──
靠自己的實力完成,沒錯,這點非常重要。有些事情我們多少可以請人幫忙,但寫作這件事,或者說,自己說話這件事,任何人都幫不了自己。因為唯獨自己,才知道「我到底要說什麼、我到底要寫什麼」;別人只能聽我說,跟我對話。
所以,「靠自己的實力獨立完成」這件事,我當然非常肯定,但也覺得,那是最基本的。
你提到〈鋼琴〉裡的鋪陳與那些修辭,我都有注意到;除了一個小地方在邏輯上我覺得有一點點問題(這無關我之前提到的「裡面的東西」),他做得還不錯。但我覺得有點可惜,那還只是「作文」。
學習說話、學習造句、學習作文,那些學習能幫助我們表達自己。當我們知道怎麼用語言和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後,重點應該就在「那麼我想說什麼?」「要怎麼說、用什麼方式說,可以讓別人懂得我想說的?」
你提到你是用「一般學生的創作」來看〈鋼琴〉。如果那些「一般學生創作」都是「作文」,那麼〈鋼琴〉是還不錯。但是,我認為寫作的真義不在「作文」──「作出一篇漂亮的文章」,就像畫畫的真義不在「作畫」──「作出一幅美麗的畫」。
為什麼學生作品中,只有作文?為什麼看不到他們的想法?他們不會想嗎?裡面沒有東西嗎?我不覺得。我認為只是沒有人告訴他們,其實他們可以「寫出自己的想法」。
他們早就可以開始寫了!如果他們想。我不希望他們跟我一樣,老了才開始。
本來只是回信,其實信寫成這樣有點可怕。可是,信寫著寫著,我發現這恰巧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──關於寫作,以及毛毛蟲月刊對於小孩的創作,該抱持著怎麼樣的態度?所以,我花了點時間寫得更清楚一點。寫著寫著,原本不那麼清楚的,漸漸清楚了。
毛毛蟲既然是「兒童哲學月刊」,那麼,文章裡頭有沒有思考,自然是最重要的。那個「思考」,不一定得要是「很厲害的想法」,而是「想的東西」以及「怎麼想的」。所以,就像我第一封信說的「大人有大人進去的東西」、「小孩有小孩進去的東西」;小孩心裡會放著什麼樣的事情、會用什麼方式想,跟大人可能不一樣。
六年級,可能已經想過很多很多事情了。如果他知道,可以透過寫作,把自己的東西寫出來,而不僅僅只是作文,我相信,生出來的東西絕對跟現在的不一樣。
到底我們為什麼要寫作呢?寫作為了什麼呢?可能是為了溝通,就像現在一樣。
最後,我很高興因為回信而寫了這篇東西,很高興有朋友可以一起討論關於寫作的事,雖然,我可能話太多了。
PS.非常巧,這兩天也跟T聊到寫作。這兩天我光是寫信就花了好多時間,但覺得異常充實(T是我在德國的朋友)。
在上封信我本來想這麼回信:我並不覺得自己對文章的要求太高。但讀了你這封信,我想某種程面上,或許是;但也或許不是。
我回想自己小學六年級寫的東西,大概也沒有什麼所謂「進去的東西」。我真的意識到「寫」這件事的意義,以及它與我的關係的時候,已經是大人了。我很少後悔,但我真的這麼想過:要是我更早一點認識寫作,我想我會更早開始認識自己;一些覺得空空的日子可能也會少一點。
回到那位同學的作品──
靠自己的實力完成,沒錯,這點非常重要。有些事情我們多少可以請人幫忙,但寫作這件事,或者說,自己說話這件事,任何人都幫不了自己。因為唯獨自己,才知道「我到底要說什麼、我到底要寫什麼」;別人只能聽我說,跟我對話。
所以,「靠自己的實力獨立完成」這件事,我當然非常肯定,但也覺得,那是最基本的。
你提到〈鋼琴〉裡的鋪陳與那些修辭,我都有注意到;除了一個小地方在邏輯上我覺得有一點點問題(這無關我之前提到的「裡面的東西」),他做得還不錯。但我覺得有點可惜,那還只是「作文」。
學習說話、學習造句、學習作文,那些學習能幫助我們表達自己。當我們知道怎麼用語言和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後,重點應該就在「那麼我想說什麼?」「要怎麼說、用什麼方式說,可以讓別人懂得我想說的?」
你提到你是用「一般學生的創作」來看〈鋼琴〉。如果那些「一般學生創作」都是「作文」,那麼〈鋼琴〉是還不錯。但是,我認為寫作的真義不在「作文」──「作出一篇漂亮的文章」,就像畫畫的真義不在「作畫」──「作出一幅美麗的畫」。
為什麼學生作品中,只有作文?為什麼看不到他們的想法?他們不會想嗎?裡面沒有東西嗎?我不覺得。我認為只是沒有人告訴他們,其實他們可以「寫出自己的想法」。
他們早就可以開始寫了!如果他們想。我不希望他們跟我一樣,老了才開始。
本來只是回信,其實信寫成這樣有點可怕。可是,信寫著寫著,我發現這恰巧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──關於寫作,以及毛毛蟲月刊對於小孩的創作,該抱持著怎麼樣的態度?所以,我花了點時間寫得更清楚一點。寫著寫著,原本不那麼清楚的,漸漸清楚了。
毛毛蟲既然是「兒童哲學月刊」,那麼,文章裡頭有沒有思考,自然是最重要的。那個「思考」,不一定得要是「很厲害的想法」,而是「想的東西」以及「怎麼想的」。所以,就像我第一封信說的「大人有大人進去的東西」、「小孩有小孩進去的東西」;小孩心裡會放著什麼樣的事情、會用什麼方式想,跟大人可能不一樣。
六年級,可能已經想過很多很多事情了。如果他知道,可以透過寫作,把自己的東西寫出來,而不僅僅只是作文,我相信,生出來的東西絕對跟現在的不一樣。
到底我們為什麼要寫作呢?寫作為了什麼呢?可能是為了溝通,就像現在一樣。
最後,我很高興因為回信而寫了這篇東西,很高興有朋友可以一起討論關於寫作的事,雖然,我可能話太多了。
PS.非常巧,這兩天也跟T聊到寫作。這兩天我光是寫信就花了好多時間,但覺得異常充實(T是我在德國的朋友)。
2010年8月27日 星期五
任性
任性。任著性子。腦子跟著性子走。
現在寫東西非常麻煩,我只是寫了「腦子跟著性子走」,就停下想:腦子真的跟著性子走嗎?我的性子不也是我的腦子控制的嗎?這麼一想,沒完沒了。原本要寫的,也寫不下去了。
不能什麼事都這樣想。
而且,我對腦子的了解少之又少,憑什麼認為,我的所有反應,都是腦子決定的呢?
這不是一開始我想寫的。
剛剛上ftp,下載工作需要的檔案。檔案是舊的,使得我的工作無法繼續。原本希望早早完成工作,好將今天從早就滿在心裡的東西寫一寫。結果跟我想的不一樣。就差那麼一步我就可以完成,因為同事的一小點失誤而耽擱,我竟然也因為這一小點的延遲,不曉得自己接下來該做什麼。
這個時候Y來了電話。說完電話後,我決定不工作了,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回家。
今天早上一起床就胸悶,我蜷著身子不想動。那種不想動不單單是身體的反應,而是心理的。我隱約感覺到今天自己想跟自己鬧彆扭。任何一個點都可以讓我彆扭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「我正在任性」;我明明知道但我還是任著性子走。
只要停下來不要繼續走就可以了。但就是停不下來,任性就是這樣,馬力十足。這時候她希望別人幫她踩剎車、或拉拉繩子,但她又知道,該踩煞車和拉繩子的是自己。
Y又來了電話。
說完電話後,她停下來了。
打開剛剛收好的筆電,開啟電源。上ftp,檔案仍是舊的,還是無法工作,但沒有關係了。她打開word,開始寫,寫「任性」。這並不是今天一早滿在她心裡想寫的東西。
寫的時候,她明白了自己的任性,還察覺了其他的,其中一個是依賴。
依賴,已經存在許久。依賴某個人、依賴某件自己覺得重要的事情;依賴,一種做事或生活的方式。依賴也沒有不好,她這麼認為;她察覺到的是,是太多了。
依賴,導致任性。
現在寫東西非常麻煩,我只是寫了「腦子跟著性子走」,就停下想:腦子真的跟著性子走嗎?我的性子不也是我的腦子控制的嗎?這麼一想,沒完沒了。原本要寫的,也寫不下去了。
不能什麼事都這樣想。
而且,我對腦子的了解少之又少,憑什麼認為,我的所有反應,都是腦子決定的呢?
這不是一開始我想寫的。
剛剛上ftp,下載工作需要的檔案。檔案是舊的,使得我的工作無法繼續。原本希望早早完成工作,好將今天從早就滿在心裡的東西寫一寫。結果跟我想的不一樣。就差那麼一步我就可以完成,因為同事的一小點失誤而耽擱,我竟然也因為這一小點的延遲,不曉得自己接下來該做什麼。
這個時候Y來了電話。說完電話後,我決定不工作了,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回家。
今天早上一起床就胸悶,我蜷著身子不想動。那種不想動不單單是身體的反應,而是心理的。我隱約感覺到今天自己想跟自己鬧彆扭。任何一個點都可以讓我彆扭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「我正在任性」;我明明知道但我還是任著性子走。
只要停下來不要繼續走就可以了。但就是停不下來,任性就是這樣,馬力十足。這時候她希望別人幫她踩剎車、或拉拉繩子,但她又知道,該踩煞車和拉繩子的是自己。
Y又來了電話。
說完電話後,她停下來了。
打開剛剛收好的筆電,開啟電源。上ftp,檔案仍是舊的,還是無法工作,但沒有關係了。她打開word,開始寫,寫「任性」。這並不是今天一早滿在她心裡想寫的東西。
寫的時候,她明白了自己的任性,還察覺了其他的,其中一個是依賴。
依賴,已經存在許久。依賴某個人、依賴某件自己覺得重要的事情;依賴,一種做事或生活的方式。依賴也沒有不好,她這麼認為;她察覺到的是,是太多了。
依賴,導致任性。
2010年8月24日 星期二
修辭
讀胡淑雯。我想著書寫與修辭。
我敲著鍵盤要打輸血,就像你看到的,出現的是「輸血」;如果我不把字換成「書寫」。應該有好長一段時間,我寫字像說話。「寫字像說話」的意思是,幾乎沒有修辭在裡頭,非常白話的。不過,雖然我寫字像說話,但我說的話並不像我寫的字,如果是,那麼很可怕。
這好長一段時間,我自己如此,讀別人寫的東西也是。修辭太多的我讀不下去。那一堆修辭對我來說都是裝飾,與他想表達的內在無關。與內在無關的修辭,如同與內在無關的形式。
但是,當外在、也就是你讀見或看見的,依著內在的需要,而決定它的樣子;那樣的東西,不論是華麗還是樸素,只要你感受到它表現的內在並敲擊到你……那麼,是不是所謂的「修辭」,就不是那麼重要了?
越清楚內在的需要,自然就會知道它的樣子。
書寫與輸血,又有什麼關係嗎?
我敲著鍵盤要打輸血,就像你看到的,出現的是「輸血」;如果我不把字換成「書寫」。應該有好長一段時間,我寫字像說話。「寫字像說話」的意思是,幾乎沒有修辭在裡頭,非常白話的。不過,雖然我寫字像說話,但我說的話並不像我寫的字,如果是,那麼很可怕。
這好長一段時間,我自己如此,讀別人寫的東西也是。修辭太多的我讀不下去。那一堆修辭對我來說都是裝飾,與他想表達的內在無關。與內在無關的修辭,如同與內在無關的形式。
但是,當外在、也就是你讀見或看見的,依著內在的需要,而決定它的樣子;那樣的東西,不論是華麗還是樸素,只要你感受到它表現的內在並敲擊到你……那麼,是不是所謂的「修辭」,就不是那麼重要了?
越清楚內在的需要,自然就會知道它的樣子。
書寫與輸血,又有什麼關係嗎?
容易
前兩天跟小美碰面,我說,「我有一陣子沒去看你的部落格了。」然後聽她說著近半年來發生的事。聽她說的同時我想著,我,是不是已經太習慣,「它」就在那兒了。
習慣它在那兒說著很多,習慣它隨時都在,我隨時都可以去。太容易知道,我的朋友發生了什麼事,所以我擺著。
讀高中時,我跟e通信。就坐在前面後面而已,但我們還是互相給對方寫信,一天可以寫兩三封。一天兩三封,打開信紙的時候還是很興奮,興奮的讀著,興奮的寫。
現在,我的email一天可以有上百封信,一半是消息或廣告,另一半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作的信,剩下的那百分之一(有時候沒有),可能是給我的信。信可能上一秒鐘寄出這一秒鐘我就收到了。那麼快我就收到了,我卻不一定馬上開啟,不一定馬上讀,也不一定馬上回信。
它一直都在,而且那麼快,回信也可以好快,我隨時回都可以。
太容易了……
看見b在部落格留言,不曉得他最近怎麼樣了。我點了收在最愛裡的他的網址:
「已經找不到網頁。」
習慣它在那兒說著很多,習慣它隨時都在,我隨時都可以去。太容易知道,我的朋友發生了什麼事,所以我擺著。
讀高中時,我跟e通信。就坐在前面後面而已,但我們還是互相給對方寫信,一天可以寫兩三封。一天兩三封,打開信紙的時候還是很興奮,興奮的讀著,興奮的寫。
現在,我的email一天可以有上百封信,一半是消息或廣告,另一半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作的信,剩下的那百分之一(有時候沒有),可能是給我的信。信可能上一秒鐘寄出這一秒鐘我就收到了。那麼快我就收到了,我卻不一定馬上開啟,不一定馬上讀,也不一定馬上回信。
它一直都在,而且那麼快,回信也可以好快,我隨時回都可以。
太容易了……
看見b在部落格留言,不曉得他最近怎麼樣了。我點了收在最愛裡的他的網址:
「已經找不到網頁。」
2010年8月21日 星期六
二十本作業簿
國中的時候,有個同學在寫愛情小說,好像也寫武俠。她用作業簿寫,寫了一本又一本,一部小說大概可以寫二十本作業簿。二十本作業簿,會有多少字呢?那些,又被誰讀見了?
一個是我,還有兩、三個同班同學。我想不超過五個。
像連載小說一樣,我讀著她的小說,一篇又一篇;一本又一本。我已經不記得那些故事了,但是,我還記得那些筆跡。
今天是八月二十日。八月十八日,我回到高雄。回高雄前,在台北,我以為自己可以利用回高雄在家的時間,多寫一點東西。一天過去,兩天過去,一直到剛剛,也就是現在,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九點十七分,我才打開word,寫著你現在正讀見的。
如果沒有讀者,我們有多少寫的動機?
現在,至少有你,正在讀的你。當然,你讀完以後,不一定有感想、不一定有評論,就只是讀過而已。但是,寫的人常常只是想說話,想說話給人聽,而現在你聽見了,他就有了寫的動機。
在從前,每篇東西不一定有被聽見的機會。
被聽見,有那麼重要嗎?
我突然想起《不同的舞步》中的一個故事:幽默作家和編輯。
從前,有個寫幽默故事的作家,當時,他二十歲。他抱了一疊他的幽默故事到出版社;出版社編輯讀了,對著文章指指點點,然後,將稿子還給他。作家回到家,重新寫過了故事,然後,再次抱著稿子,給出版社編輯。
再一次,編輯指指點點,退他稿子。作家回家,修改,再抱著稿子給編輯,然後,又再度被退稿。
剛開始,他們很年輕,作家跟編輯都是;漸漸的,他們有了白髮;再見面時,他們的背彎了,戴上了老花眼睛;最後,兩個人都像個小老人的時候,編輯讀著作家的稿子,讀著讀著,嘴角牽動了;他笑了,越笑越大聲;看著編輯那樣開心,作家也笑了。兩人彷彿讀著全世界最好笑的故事!
編輯實在笑得太過了,突然,就死了。
這個老老老作家的幽默故事,轉到另一個年輕編輯的手中。年輕編輯讀過之後,臉上毫無表情。於是,我也就沒有機會讀見那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笑的幽默故事。
在這個年代,每個人講的話幾乎都有人聽,每個人說的故事幾乎都有人笑。我想起,我的國中同學。
如果她寫作的年代是現在,說不定她會是個網路小說寫手;當然,如果她從現在開始,或許也來得及成為網路小說寫手。
但是,如果她不是我的同學,在眾多部落格中,她可能不會被我記得。現在那麼多人在寫、那麼多人希望被讀見;而他們(我們)也確實被看見與聽見了。但也因為這樣,在這樣的年代,不會再有二十本作業簿出現。
老實說,那二十本作業簿至今我仍深深記得;
那是一個不太可能會發生在現在的故事,就連在從前也是難能可貴,
在那個,沒有讀者、沒有聽眾的年代。
一個是我,還有兩、三個同班同學。我想不超過五個。
像連載小說一樣,我讀著她的小說,一篇又一篇;一本又一本。我已經不記得那些故事了,但是,我還記得那些筆跡。
今天是八月二十日。八月十八日,我回到高雄。回高雄前,在台北,我以為自己可以利用回高雄在家的時間,多寫一點東西。一天過去,兩天過去,一直到剛剛,也就是現在,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九點十七分,我才打開word,寫著你現在正讀見的。
如果沒有讀者,我們有多少寫的動機?
現在,至少有你,正在讀的你。當然,你讀完以後,不一定有感想、不一定有評論,就只是讀過而已。但是,寫的人常常只是想說話,想說話給人聽,而現在你聽見了,他就有了寫的動機。
在從前,每篇東西不一定有被聽見的機會。
被聽見,有那麼重要嗎?
我突然想起《不同的舞步》中的一個故事:幽默作家和編輯。
從前,有個寫幽默故事的作家,當時,他二十歲。他抱了一疊他的幽默故事到出版社;出版社編輯讀了,對著文章指指點點,然後,將稿子還給他。作家回到家,重新寫過了故事,然後,再次抱著稿子,給出版社編輯。
再一次,編輯指指點點,退他稿子。作家回家,修改,再抱著稿子給編輯,然後,又再度被退稿。
剛開始,他們很年輕,作家跟編輯都是;漸漸的,他們有了白髮;再見面時,他們的背彎了,戴上了老花眼睛;最後,兩個人都像個小老人的時候,編輯讀著作家的稿子,讀著讀著,嘴角牽動了;他笑了,越笑越大聲;看著編輯那樣開心,作家也笑了。兩人彷彿讀著全世界最好笑的故事!
編輯實在笑得太過了,突然,就死了。
這個老老老作家的幽默故事,轉到另一個年輕編輯的手中。年輕編輯讀過之後,臉上毫無表情。於是,我也就沒有機會讀見那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笑的幽默故事。
在這個年代,每個人講的話幾乎都有人聽,每個人說的故事幾乎都有人笑。我想起,我的國中同學。
如果她寫作的年代是現在,說不定她會是個網路小說寫手;當然,如果她從現在開始,或許也來得及成為網路小說寫手。
但是,如果她不是我的同學,在眾多部落格中,她可能不會被我記得。現在那麼多人在寫、那麼多人希望被讀見;而他們(我們)也確實被看見與聽見了。但也因為這樣,在這樣的年代,不會再有二十本作業簿出現。
老實說,那二十本作業簿至今我仍深深記得;
那是一個不太可能會發生在現在的故事,就連在從前也是難能可貴,
在那個,沒有讀者、沒有聽眾的年代。
2010年8月18日 星期三
倒了
小女孩在哭。
小男孩打開一罐飲料,「給你喝。不要哭。」
小女孩接過來,邊哭,邊喝;邊喝,邊哭。
小男孩看著小女孩。
小女孩喝了幾口,把飲料擺在地上,跟小男孩玩了起來。
他們追著跑著。
然後, 飲料倒了。
飲料倒了,甜甜的流出來。
流出來,流出來,流出來,流出來。
「飲料倒了……」小男孩直直的站著。
「飲料倒了……」小女孩用手去摸。
小男孩:「媽媽,姊姊把飲料弄倒了。」
小女孩:「媽媽,我把飲料弄倒了……」
小女孩又哭了起來。
(20190329重讀,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)
2010年8月11日 星期三
寧願
因為……所以你必須。如果可以,你並不想,但已經如此了。
後來你才懂,有些東西是裡面不想接受的,但不得不。
不得不的東西,無可選擇。不是你要不要。
可總是處於這種時候,才多懂了一些。
但是你說:
寧願不懂。
2010年8月7日 星期六
關於「無限集合」
「集合」,就是某個東西的數量。通常會有所指定,比如說,我家的「人」的「集合」是「4」人,「女生」的集合是「3」人,「男生」的集合是「1」人。
「無限集合」的意思,顧名思意是「某個東西的集合,數量是無限的」。
書上寫著:「無限集合」又分成「『可數』的無限集合」跟「『不可數』的無限集合」。
「『可數』的無限集合」有:偶數的集合、奇數的集合、正整數的集合、整數的集合、有理數的集合(有理數的意思是,可以「分數」的形式表現)。以上這些數的集合,量都是一樣的。
「『不可數』的無限集合」指的是:實數的集合(實數是「有理數」+「無理數」)。
「實數的集合」,比「有理數的集合」要大。
一開始,我不太能接受。為什麼「無限集合」能分成可數和不可數呢?又怎麼會有大小之分呢?
後來我想起來,無理數指的是「根號2」這種無法以分數表現的數,用小數表現是1.4142......(後面沒有窮盡)的這種數字。這種數字,說它是「不可數」,好像也可以接受。
嗯,那麼,在「想像上」我可以接受「無限」分為「可數」與「不可數」,並且「實數的集合」(「有理數」+「無理數」的集合)比「有理數的集合」大。
可是,既然都是無限集合,要承認「某個無限集合」比「另一個無限集合」要來得大,好像有點困難。
後來,我這樣想——我做了一個不曉得適不適合的假設(請用想像的,不要考慮現實):假設地球上的人類會不斷的生育,假設,會一直生一直生,沒有世界末日來把人類毀滅。假設有這樣的世界,那麼未來女人的數量是無限,男人的數量也是無限,人類的數量也是無限;而人類的無限集合當然比男人的無限集合大,也比女人的無限集合大;而這三種無限集合將會一直大下去,沒有終止的一天。
我好像解決了自己「某個無限集合」比「另一個無限集合」要來得大的問題。可是,如果真的是這樣,那為什麼「偶數的集合」跟「正整數的集合」一樣大?「正整數的集合」跟「整數的集合」一樣大?
怎麼想「虛數i」?
怎麼想「虛數i」?
X的平方=-1
X=「根號-1」與「-根號-1」
算式上可以通,
後來也慢慢想通了,
確實,根號的平方,把跟號拿掉,就剩下裡面的東西,可以通。
這個實在太酷了!
2010年8月3日 星期二
那麼難,那麼容易
這個時候,需要寫一點東西。
早晨的一開始不如預期,需要寫一點東西。
常常是這樣,不如預期。
世事無常,老和尚這麼說。說是說,不是那麼容易。
今天說的,明天就不見了。現在想的,下一秒就變了。
那麼容易,怎麼那麼容易?
今天有很多事,生活中總有很多事,很多不如預期。
儘管如此還是會走下去。不那麼難,也不那麼容易。
早晨的一開始不如預期,需要寫一點東西。
常常是這樣,不如預期。
世事無常,老和尚這麼說。說是說,不是那麼容易。
今天說的,明天就不見了。現在想的,下一秒就變了。
那麼容易,怎麼那麼容易?
今天有很多事,生活中總有很多事,很多不如預期。
儘管如此還是會走下去。不那麼難,也不那麼容易。
2010年8月1日 星期日
《1000%》.政大附中.劇魂(加談一點點明倫高中)
劇名:花樣年華國際青少年戲劇聯演——1000%
時間:2010‧8‧1‧14:30
地點:台北縣藝文中心演藝廳
團體:政大附中「劇魂」
戲開頭,兩個中年男子相約見面,說起高中時候的夢想——他們希望能夠做一齣擠滿千萬觀眾的戲,說完,兩人相識而笑,接著憶起高中戲劇社團生活。這時,一群人走上舞台,兩名男子走下台,坐進觀眾席,觀賞他們以前的自己,從前在戲劇社中發生的點點滴滴。
這是一個戲中戲,一個懷念青春的故事。其實我蠻好奇的,演員自己都還是高中生,卻說起一個懷念高中生活的故事。
會說一個這樣的故事,我猜,很可能是創作者覺得自己的高中生活,對長大後的自己來說,將是一個美好的回憶。我想起自己從前也想過,要把高中生活寫下來,因為,我想不管我未來變成什麼樣子,我都會非常懷念我的高中時光。
這群人,在現實生活中,未來應該也會真的很懷念他們的高中時光吧!不過,呈現在這齣戲裡的「戲劇社團生活」,有多少是真實的縮影,就不得而知了。
這齣戲寫得很流暢,架構、內容都蠻成熟的,人物角色性格有,細節也有。演員表現也不錯,基本上好看、不乾(不過有些地方有點拖,尤其是花花耍花癡那段,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受不了女生耍太久的花癡吧!好方面來想她也實在太會演花癡了!)
戲裡頭的男演員頂亮眼的,裡頭還有兩個帥哥!綽號「俠客」的男生,遠看有點像岳小鳳;「萬事通」是清秀型的男孩,有一幕他站到舞台中獨白時,我後面的兩個男生一直小小聲地叫:「喔!好帥!」其實,我個人覺得「水電工」不賴,他大概是裡面最鬆的。
今天的戲是好看的。硬要說的話,劇情有點工整。不是說硬要高潮迭起之類的,是……整體來說有點太穩,新意不夠(如果相較明倫高中的《淘氣追夢三人行》)。還有,劇名取得不算好!光從劇名來看不出內容,也不吸引人。
「政大附中」與「明倫高中」
既然提到明倫高中,我發現這兩齣戲裡面都有電玩元素。這兩天來看戲的有很多是家長,我很好奇,那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是:「啊!是在演什麼?」還是:「喔!原來他們的世界是這樣!」
另外,這兩齣戲處理「友情」也有些許不同。政大附中的「俠客」被發現手臂上有刺青時,大家輪番上陣表演友情溫暖;明倫高中則是當學生與老師都陷入危險時,陳怡文說:「干我什麼事?我要回家!」
第一種跟第二種,沒有那一種處理得比較好或不好,不過,我個人覺得明倫高中演出了某一種實際,也比較辛辣,某種程度「也可能」比較誠實。
這樣想起來,《淘氣追夢三人行》要講的東西還真不錯,雖然我在問卷上寫說「覺得太直接了」,但仔細想想,「誠實面對自己」還真是一個很重要、很值得談的東西,而且他們說得一點也不八股。特別是陳怡文這個角色,我現在補充說明,她這個人冷眼旁觀又黑色,當幻影讓她看到她最害怕的東西時,她說:「我會看到什麼呢?」然後,她發現:「原來是我自己。」她伸手摸一摸對面那個自己,最後說:「面對自己有什麼好怕的?」幻影就消失了。
嗯,這段劇情還蠻酷的。
訂閱:
文章 (At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