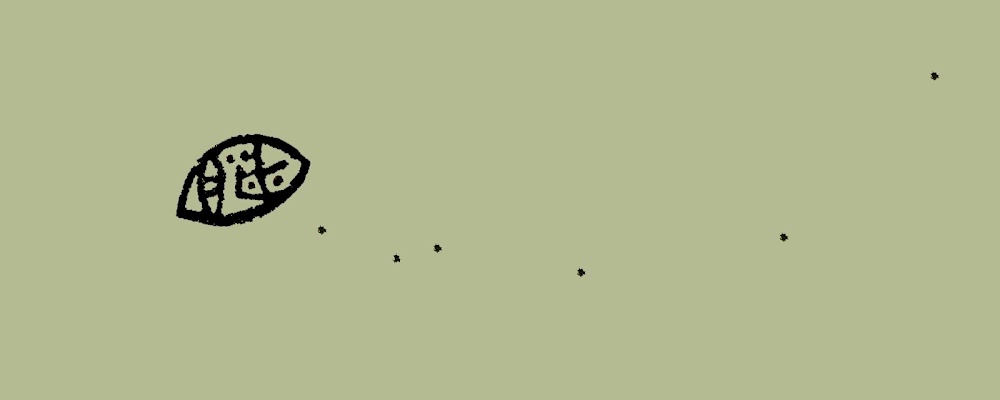因為文章太長了,所以先預告「開房間」的演後座談:
8月22日晚上7:30,城中藝術街區 Urbancore Gallery,
台北市中華路一段89-4號,近西門捷運站2號出口
◆◇
拿了203的房卡,往二樓走去。203在角落。
我在203前站了好一會,因為我不曉得房卡該往哪感應。太少住飯店了。我看看門鈴,看看門鎖,就是不知道該把房卡往哪放。服務人員走過來,協助我感應房卡。
「原來是在門把上方。」我心裡很謝謝她。
推開重重的門,我走進房間。房間有人住過的樣子,卻沒有人。窗簾半掩,透進些微陽光。房內沒有開燈,沒有聲音,沒有人。床的被子是拉開一邊。窗前有桌子,桌上有書。
走進一個沒有人卻感覺之前有人在的房間,時間變慢了。只有我一個人在房間裡。我不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。時間變得很慢,因為我在等。人什麼時候會出現?會從哪裡出來?是誰?他會跟我說話嗎?
我在昏暗的房間裡待了大概有兩三分鐘,或許沒有那麼久,我不確定,我的時間感混亂了。然後,我聽見有人開門鎖的聲音,有人要進來了。
門打開,是理容。
她是理容,但此刻不是理容。她看著我,我看著她。她看著我,露出走錯房間了嗎的表情,看看房門,又看看我。「廖小姐?」她問。
我說是。
從理容進來的那一刻起,我就在想,我是誰。
顯然此刻的理容,不是現實生活中我認識的那個理容,而是開房間「屋上積雪」這齣戲中的某個角色。她對我說話,而且我回答了,所以我是存在的,我是廖小姐;可是這個理容不是那個認識廖小瞇的理容。
我面前的這個女人,穿著彩色寬鬆的絲質上衣,有點像會去菜市場買菜的中年婦女。她對我說了一些話,我現在已經忘了她說什麼了,因為當時的我一直想著她是誰我是誰的問題。我只知道她似乎跟我要了房卡,然後燈就亮了。其實,我自己應該要懂得把門卡插進感應插槽,但我太少住飯店了,我根本沒想到這回事。
然後她開始說話,說些什麼我現在不記得了,類似自言自語又像是說給我聽的碎唸。我還不曉得我對她來說究竟是什麼,所以我旁觀,沒有對她的說話有所回應。
她把包包放下,走到一面牆後面,似乎在跟誰說話。
「你怎麼在這裡坐這麼久?」「在這裡坐這麼久不好喔……」「要不要起來了?」她在跟某人說話。
顯然她要我走過去看她在做什麼。但如果我不走過去呢?
我還是走過去了。浴缸裡躺了一個用海綿做的假人。感覺好詭異。浴缸中有個假人。這個假人是假人?還是屍體?還是某個誰?我要怎麼辦?聽她繼續說?還是對她說:「你在幹嘛?」
如果我對她說:「你在幹嘛?」那麼其實我早該在她進門房時就對她說:「原來是羊理容。」或者在她叫我廖小姐時,對她說「幹嘛叫我廖小姐?」
但我沒那麼做,代表我把這當戲了。不過,如果我不把這當戲,要把它當什麼?我不就是來看戲的嗎?但我對自己說,這似乎不是戲不戲的問題,我是想來看這究竟要做什麼。
看來,理容確實是在演戲,而我在她的戲中。但是,如果我選擇只看戲,不進入戲中,不跟她說話,不跟她動作,會怎麼樣呢?
在我看到理容對假人說話時,理容對我說了:「廖小姐,你可以幫我抬老先生到床上嗎?」
我要說好嗎?我要跟她一起抬這個她口中的老先生假人嗎?我大概想了一兩秒。然後我說「好」。
我抬起假人好輕好輕的腳;但理容的表情好重好重。
將假人抬到床上躺好後,理容說起老先生的故事。
這時,我才慢慢確定,這個假人不是假人,是個老先生(但我還是不理解他剛剛為什麼躺在浴缸裡);在理容說得更多一些之後,我才慢慢知道,這個老先生是個詩人;說得再更多一些之後,我才知道自己在這戲中所扮演的角色:原來我是一個來探訪老詩人的人,我可能是記者,或是曾聽過老生演講的人。
理容給我看老詩人的詩集。
「所以,他叫林豐明?」我看著詩集,這樣問。
「你可以叫他林先生。」理容說。
這有點弔詭了。因為,我這個來探訪的人,並不認識我所要探訪的人。但我在這裡確定了,假人叫林豐明。
我翻著林豐明的詩集。我不認識林豐明,也沒讀過他的詩集。
理容跟我閒聊,她慢慢說出林豐明的故事。理容一邊幫他按摩,一邊說著他的故事;然後,她邀我一起幫老詩人按摩。
我坐到假人的左邊,托起他海綿的手,開始按摩。
理容說:「不要太用力,輕輕的就好,小心骨頭。」
假人的海綿手,還真的有骨頭。
後來理容抬老詩人到書桌前,「你好幾天沒有寫東西了,要不要寫一點東西……」我跟著理容抬著老詩人到書桌前,理容在他面前放了本子和筆。老詩人坐好後,理容把我叫到旁邊,老詩人剛剛躺著的浴缸邊。
我覺得坐在浴缸邊很奇怪,可能這浴缸不是浴缸。
理容說老詩人是核電場的工程師。理容說老先生從前去演講時所發生的事。理容說老先生對那些工人的不捨與無奈,理容說著核電場的問題。
「你怎麼知道這些事?」我問。
「老先生跟我說的啊!」理容說。
說到一半,理容像是聽見什麼聲音,突然站起衝到老先生的身邊,「你在找什麼?你不要亂丟書,你不要生氣,你在找什麼我幫你找!」理容舉起假人的手一邊把書丟得滿地,一邊這樣對假人說話。但這時的我似乎已經接受假人是老先生了。
在書丟得滿地一團混亂中,電話響了。「要接嗎?」我問理容。
「你可以幫我接一下嗎?」理容說。
我接起電話。
這邊是櫃台,X小姐,有林先生的包裹(原來理容是X小姐)。我跟理容說了電話內容。理容將老詩人安撫後,對我說:「我去櫃台拿一下包裹。桌上的書你都可以翻,就那個老先生剛剛寫的本子你不要翻,老先生不喜歡人家看他還沒有寫完的東西。」
我說好。
理容出去了。又剩我一個人在房間裡,嗯,應該說是兩個人。理容剛剛的話應該是提示我趁她不在時去翻看本子。但我實在老實過頭了,人家既然說了「那個老先生剛剛寫的本子你不要翻」,我就真的沒去翻。但我站在桌邊,讀著打開那頁上面的句子。
理容回來了。
包裹是老先生的女兒退回來的。老先生的女兒說,我是你用核電廠的錢養大的,這已經沒有辦法了,但我現在不要這些錢。
所以老先生現在自己一個人住在旅館裡,理容照顧他。
「這個床很舒服,你要不要躺躺看?」理容這樣問我。(我其實忘了在這之前她說什麼了,為什麼突然這樣問我。)
我當時想,不好吧?這不是老先生的床嗎?但我還是說好。
「我會睡著喔,我說。」
「來,躺下來。棉被蓋上。」
太好了,我真的很想睡覺。我把眼鏡拿下來,整個人窩進棉被裡。
理容說:「手要伸出來。」
我說不要,我好冷喔。
然後理容說,有時候老先生和她談心事的時候,會輕輕按著她的手。說著,理容輕輕按著我的肩頭。這時我才知道,為什麼理容剛剛要我把手伸出到棉被外來。現在她不能捏我的手,只能捏我的肩頭。
實在很舒服,我快睡著了。
後來,理容小小聲的說,「你休息一下,我去看一下老先生。」
我說好。如果可以的話我真的很想睡著。
然後我聽見理容跟老先生說話的聲音。聽著聽著,聲音漸漸從遠處慢慢走到我的身邊。理容說,「你很累喔,是不是沒有睡好?不然再睡一下好了。」「你要不要先起來吃藥,然後再睡覺?」理容輕輕按著我的頭,幫我按摩。
我的眼睛一直閉著。我知道我變成老先生了。但我不想睜開眼睛,因為老先生在睡覺,而我也想睡覺。
理容要餵我吃藥。「吃完再睡。」理容說。
看著理容手掌中的三顆藥,我說我不想吃。我說可不可以明天再吃。
最後理容依了我,她要我好好休息。
理容放了老先生喜歡的音樂給我聽,對我說,「我把你剛剛寫的東西,放在旁邊。」然後離開房間。她離開後,我坐起來讀本子上的詩句。我讀了兩遍。
又有人進來。一個穿著像上班族的男子。他無視我的存在。我是誰?我又開始問這個問題。他像是住在這房間的人,他進來梳妝整理後,又出去。
又剩下我一個人了。
這時電話響起。櫃台:「廖小姐,你的時間到了喔,請把房卡交給櫃台人員。」喔,戲要結束了。我想著,我回家後要查林豐明的資料。
離開前我去翻了桌上林豐明的詩集。
簡介寫著林豐明一生服務於台灣水泥公司,二○○五年於該公司花蓮廠廠長任上退休。這詩集作者,並不是屋上積雪中的林豐明,那位老詩人。我誤會了。
◆◇
是不是真的林豐明,有影響嗎?如果在看戲之前我就認識林豐明,那麼會影響我對戲的感受嗎?好像會,因為我一度認為戲中所說的林豐明先生的故事,是真的林豐明先生的故事,我還想著回家之後要去找他的資料,我認真了。
後來知道這不是真的故事。有影響嗎?其實我知道故事裡說的,是真實的,儘管故事是虛構的。
素伶問得很好,這跟進劇場看戲有什麼不一樣?當然我可以選擇繼續當一個不說話的觀眾。這讓我想到再拒的「公寓」,觀眾雖然與演員在同一個空間裡,一起在客廳,在小房間裡,但演員看不見他們,觀眾是不存在現場的一雙眼睛。
但是在「屋上積雪」中,觀眾存在現場。編導給了觀眾一個角色,給了他進到這個房間的理由。只不過,這個理由,得在觀眾打開這個房間的房門之後,才會知道。
◆◇
節目名稱:開房間.屋上積雪
主辦單位:河床劇團
導演:鴻鴻
演出:陳雅柔、楊禮榕
地點:八方美學商旅
時間:2011年8月20日下午5點20分(該場演出者為楊禮榕)